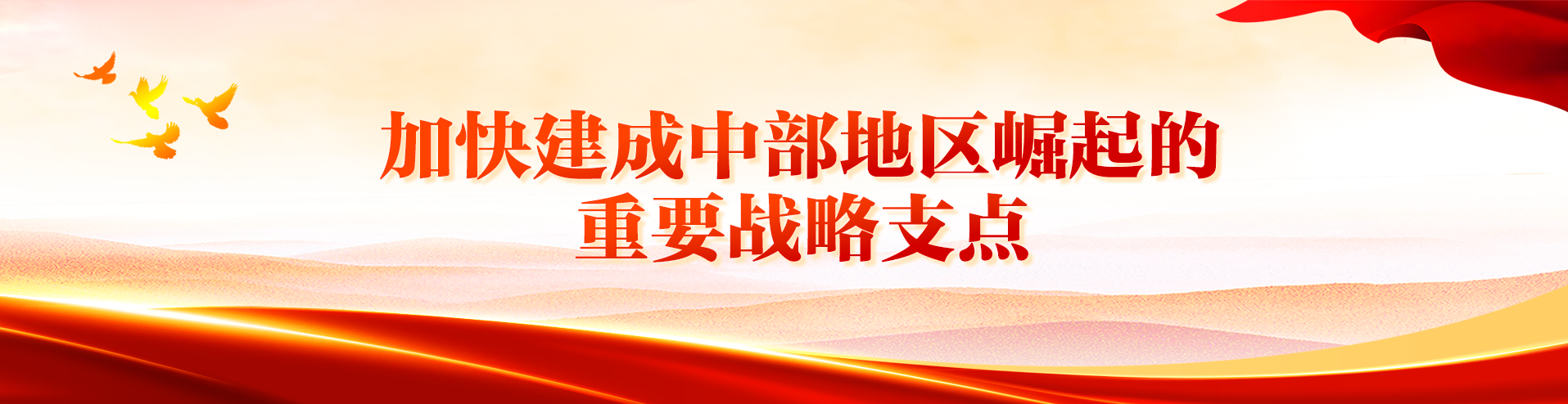迎着清晨第一缕阳光,一辆辆白色的餐厨垃圾收运车从黄金山餐厨废弃物处理厂鱼贯开出。
宋卫林就在其中的一辆车上,在布满油污的驾驶室里,他穿着一身洗得泛白的灰色工作服,座位边夹着一双橙色的塑胶手套,这一切都斥说着他的身份,餐厨垃圾收运人
记者体验,克服“三关”真难
“脏”是这个职业最直接的标签。
当记者爬上这辆比一般车都要高许多的收运车时,宋卫林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洗过车了,味道会不会好一些?“
面对这份善意,记者微笑着点点头,他却很担心,“现在还行,等会儿收的垃圾越多,臭味还是会越来越重的。”这趟旅程就是在这段“有味道”的谈话中开始的,这份“味道”也持续了整个探访过程。
宋卫林的行车路线是固定的,每到一处点位,他就会跳下车,操起塑胶手套,把一桶桶装着餐厨垃圾的垃圾桶,挂到垃圾车的卡口上,在按下按钮后,车上的履带会自动将垃圾桶运到车顶,将垃圾倾倒入车内。
一趟又一趟,一桶又一桶,当作为旁观者时,记者只觉得这份工作十分机械,有些枯燥,却并不太难。可是真的当记者自己上手时,感觉瞬间不同了。
难受是从戴手套开始的。宋卫林告诉记者,这是一双才戴了2天的新手套,然而当记者近距离看时,才发现手套的手心部分已经被油污浸染,上面黏着一层密密麻麻的花椒颗粒,让人一看就觉得头皮发麻。
等到戴着它走近垃圾桶时,记者的汗毛根根竖起,混合着各种饭菜和肉食的垃圾,颜色艳丽诡潏,让人看了一眼便不想再开第二眼。但是味道却无法隔绝,那散发出一股奇妙的混合着菜香的恶臭,随着垃圾晃动层层叠叠泛上来,给人嗅觉一波又一波的冲击。
但是记者很快就顾不上这些了,因为垃圾桶推不动。
在宋卫林手上轻松得如同推玩具车的垃圾桶,在记者的手中却是纹丝不动。虽然宋卫林在旁教授小技巧,记者也没有推动多远便被宋卫林阻止了,“这有百来斤呢,你这样会让垃圾泼出来的,都是油,泼出来环卫工人不好清理。”
面对羞愧的记者,宋卫林却是笑着安慰,这些看着很简单的工作,却处处含着小技巧,一般新招的收运人都要跟车1个月才能自己行动,这样一方面是帮助他们克股气味关、视觉关、心理关,同时也要培养他们体力,学习推垃圾桶的技巧。
“新人把垃圾溅自己一身都是很正常的。”宋卫林笑着说,不过能到那一步都不算新人了,真正的新人在跟车时便会被难以忍受的臭味和垃圾的视觉冲击打败而离开,根本到不了实际上手操作这一步。
干着最脏的活儿,实际上却是为了最极致的干净
在宋卫林看来,他的这份职业既“新”且“净”。
这份“新”不在职业本身,而在于餐厨垃圾项目。过去的“收泔水”,往往是利益驱使,他们拉走的餐厨垃圾要么流向养猪场,要么流向地沟油炼制作坊,从来都是“地下交易”见不得光。
黄金山餐厨废弃物处理厂项目的垃圾收运目的则决然不同,它是国家第四批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项目,通过对餐厨废弃物进行统一收运、集中处理,在进行满足无害化处理的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做到资源充分回收、合理利用。
“我们干着最脏的活儿,但实际上却是为了最极致的干净,守护餐桌安全与市容洁净。”宋卫林说着这些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他说他们收运“脏”,守护“净”。
然而,与所有新兴事物发展规律相似,餐厨垃圾收运工作最开始也是艰难的,无论是打断既有利益链条,还是培养人们垃圾分类意识,都不是一件容易事,他们受过白眼,也遭过冷嘲,吃过闭门羹,更经常被无视。
宋卫林作为城市的第一批餐厨垃圾收运人,完整地经历了这个职业从被排斥到被接受的整个过程。从最初一个人一辆车跑遍黄石,日收运量不足30吨,到如今十余辆车分散到不同线路,实现日均收运量在100吨上下浮动,垃圾处理厂终于满产运行。
他感叹,仅仅从收运垃圾中就能感受到,城市的文明程度在提高。在他看来,持续增高的不仅是餐厨垃圾收运量,更是居民逐步攀升的垃圾分类意识。
当然,这份“净”也体现在了黄金山餐厨废弃物处理厂本身建设上。在经历了几轮智能化改造后,过去长期浸润在臭气中的处理厂已经变得清爽起来,而随着二期沼气发电项目的启动,项目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垃圾发电“变废为宝”。
如今,黄金山餐厨废弃物处理厂已实现满产运行,每年可处理全市餐厨垃圾36000吨,地沟油290O余吨,产生沼气量225万m³,发电量430万度。